|
馬克•克萊門 Mark R. Kramer提交 思高基金會 The Skoll Foundation 基金會策略集團 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 出版 (2005年4月) 1. 主管摘要 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為慈善事業 (philanthropy) 帶來了新的視野,也帶來了新的評估觀點。事實上,慈善領域中很多令人熟悉的評估方法,都缺少資助人 (funders) 認為在社會創業領域中成功所需要素的關鍵標準 (key criteria)。 在這個新興領域中,資助人 (funders) 也發明了他們自己的評估投資成果的方式,通常是由他們的同儕獨立暨平行的評估。因此,對一些常見做法的審視,會引出對一般問題,雖然不同卻常重疊的解決方法。這份報告的目的就是要探究現今社會創業各種多樣的評估方式,為目前實際使用的方式建檔,這樣新加入這個新興領域的人,就不需要再重新發明前輩們已經發明過的方式。但有時,這種較新穎的思考方式,比起目前慈善領域中較常見的方法,似乎比較更適合現實中混亂的社會改革。反過來說,社會創業中較務實的評估方式,有時缺少較完善的符合方法論所要求的學術規範 (discipline) 與可信度 (reliability)。因此,我們希望這份報告能提供社會創業領域,以及更廣泛的慈善事業領域,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 而最近由於它的募款訴求,該術語被更鬆散的用來形容,任何有領導魅力及拓展野心的非營利組織領袖。 其中一位受訪人說: 社會創業似乎是「老生常談same old stuff」,只是被更懂市場運作的領導人,包裝起來欺騙可憐的基金會,誤導它們相信這是不同的東西。 然而還有第三個定義,它用於形容一群不尋常的社會領域領導人以及他們創立的組織。首先,這些領袖打破了非營利及營利領域中的壁壘,堅持這兩種工具都能有效地達成社會變革,並採取自由選擇使用或不使用其財務結構來達成目標的政策。 這些社會創業家的第二個出色的特點,就是想創造體制變革的企圖心,他們引進新的想法,並且說服他人採用。社會創業家會重新思考問題,並且會尋找之前沒有試過的方法來避免或解決問題。社會創業家根本的定義就是「找出新的做事方法」這樣的概念,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並且努力改變他人的態度與行為來接納自己的想法。這一點強調的就是,採用不同於一般容易循著現有的途徑或常規解決問題的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的新方法。 最後,社會創業家還有一個大規模經營的野心,這是大部份一般非營利組織都無法想像的;這個野心並不只是服務當地區域的人民,也不是只有建立國家層級的組織而已,而是創造整個國家,甚至是全世界行為上持續的變革,改善數以百萬計人口的生活。 於本文中,「社會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這個名詞指的是第三種定義:一個創立並領導一個組織的人,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並且要透過引進新想法、方法及態度改變,來創造大規模且長久的體制性變革。 社會創業最好的範例應該就是微型金融的發展。長久以來,大家都認為不能借錢給窮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拖欠率 (default rate) 與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會超過任何可能的經濟收益 (economic return),而且數量太小了,也無法提供任何重大的社會益處。到1970年代,國際發展組織試著用傳統的借貸方法,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但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失敗經驗。隨後兩個新組織,拉丁美洲的「阿啟恩ACCION」以及孟加拉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經過十年的實驗,發展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借錢給窮人的方式。他們的創新方法,即現在廣為人知的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因為他們發現就算是區區50美元,都可能足夠讓一名婦女取得縫紉機與布料,以養活家人;這種貸款對投資人來說,也是有不錯的財務收益,尤其是事實證明,出人意料地貸方竟然可以負擔20%或更高的利率,而由阿啟恩及鄉村銀行所發展的創新作法,也一直維持著97%的還款率。 這兩個組織都成長到了相當大的規模,但是他們的點子的影響力,連他們自己都相形失色;時至今日,全世界有好幾千個微型貸款機構,服務四千一百六十萬個家庭,並援助超過兩億個家庭成員。在這些借貸機構中,幾乎沒有一個組織,是與原本建立這個領域的社會創業家有任何關係,但都是使用他們發明的方法的演變型式。 而以下是社會創業家所達成的社會變革的典型構成要素:一位有遠見的領導者、一段研究如何更有效創造社會效益新方法的實驗期、一個影響力快速成長的組織、以及一個散佈世界幫助數以百萬計人們的想法。 當然社會創業家是受很多不同型態的捐助者贊助的,從私人到又大又健全的基金會、政府以及國際援助組織。但在這麼多援助的資源中,有一小部分的資助人,對於找尋及資助社會創業家特別努力。這些人的行動,通常彼此間就不太一樣;然而他們有一些根本的共同價值 (shared values) ,使他們有別於其他的捐助者。「社會創業家資助人funder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這個術語,在這份報告中,只適用這一群與眾不同,自我選擇的資助人,而「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這個術語,則包含了這些資助人、思想領導者以及社會創業家本身。 2.2 慈善事業中的評鑑調查 慈善事業整體來說,評估調查是少見的。在美國六萬多個基金會中,我們估計大概只有幾百個基金會,會定期做正式的評估調查;而只有不到五十個基金會,內部就聘有評鑑專家。就連最定期做評鑑的基金會,都沒有正式的評鑑他們所提供的大部分補助金 (grants)。 在那些相對來說稀少,但會固定的實行評鑑行動的基金會中,它們評鑑的目的、使用的技巧以及嚴謹的程度都參差不齊。有些基金會評鑑補助金支援計畫的執行進度過程,來觀察它是不是有照計畫進行;有些單純只有觀察計畫的投入 (inputs) 或產出 (outputs),像是成本或是服務過的人數;還有一些基金會會嘗試追蹤短期結果,像是一到三年內對情勢或行為造成的改變;最後,還有一些會藉由評鑑計畫或補助金所帶來的更持久的社會變革,來試著測量所帶來的最終社會影響。用來評鑑補助金或計畫的方式也不一樣,從受資助人自行報告到依靠外部的評鑑專家及嚴格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拿小心挑選的控制組,比較計畫參與人的長期效果。 評估方式也可以適用到不同的層級:特定的補助金、受資助人組織、計畫地區、基金會或是一整個領域都有。就連實行評鑑的目的,都從評量補助金的援助結果或測試邏輯模型,拓展到了組織學習、受資助人能力的建立、知識管理,以及基金會自身表現強化等等更廣大的目標。 社會創業就利用了這些豐富的評鑑方法,然而社會創業家以及他們的資助人,引進了一種對於評鑑的過程及目的,顯現出有非常不同態度的方法,這種方法同時也非常實際及有彈性,舉例來說,如「總結性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是一種計畫執行後,試著評量補助金造成的成果或影響的回顧性研究 (retrospective study),這種評量就很少運用在社會創業,因為這個方法一般來說成本太大,而且也很難有即時的回饋;資助人傾向與他們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保持密切連繫,就很少使用外部的評鑑人員來扮演協助的角色,或者是發現他們在計畫進行中學習到的東西。在第三章第四節裡會提到,在社會創業領域裡,組織能力的評量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但大部分都要依靠組織生命週期的階段、理念的傳播以及社會創業家的個人成長來判斷;所以「混群評價Cluster evaluation」,一種對有共同社會目標的多個補助金或受資助人做的評量,就會很難應用,因為資助人可能投入工作的地點或領域都太多了。簡短來說,社會創業領域裡的人們,發明了自己的評鑑方式,以符合他們的在本質上就與眾不同的觀點。 譯員B:許庭瑋 (3,137字)
我們不給人魚;我們也不教人如何釣魚。我們嘗試改變整體市場的供魚方式。 如果你決定要做到這一點,你就不能只是衡量你提供多少魚。 3.1 一個有不同視野的新興領域 社會創業家是一個多元的群體。你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看到他們處理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議題。他們創新的點子引領他們跨越傳統規範的界線,而他們發展出來的解決辦法,常常都會非常巧妙地符合他們所幫助的族群的文化及情勢。他們的資助人也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有些只用債務或股權的方式投資,有些就使用慈善基金;有些人在社會創業家做實驗的初期即對他個人進行投資,有些則專注在組織後續發展的成長與效率上。雖然很多樣化,但有一個共有的觀念,使得社會創業這個新興領域與其它慈善事業和評鑑方式有所不同。 例如,其他的捐助者考慮涉足此領域時,常常會從選擇要在哪個社會議題或是計劃領域及地理位置等開始下手;譬如一個基金會可能決定資助本地城市或開發中國家的住宅、健康醫療或是教育。事實上,很多基金會會將人力與營運分散到獨立的計劃領域,而各組負責的議題或地區都不一樣。 然而社會創業家資助人的想法不一樣,他們似乎不會特別在意要關心哪個議題或在哪個地區提供幫助。就像一個期待某種程度報酬率的投資人,他不會在乎這些報酬是因為買了製藥公司,還是電腦軟體公司的股票,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似乎較專注在所創影響的規模以及其 持續性,還有他們的錢如何運用,而不特別在意所處理的社會議題本身。一些資助人把自己限制在某個單一的領域,而其他的資助人在一開始時,試著不限定在某特定領域投資,最後也還是縮回了特定計畫領域內。然而我們的訪問顯示,在人類各種廣泛的需要中,很多社會創業資助人,對所處理的社會議題,好像也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 我們根本不會管他們選擇的議題是不是符合我們的策略;我們要求計劃要符合人類的社會需求,但除此之外,我們無須了解那些議題的細節。 我們認真考慮他們想造成的影響的類型、他們對於辨識需求及了解該用什麼手段造成影響的老練程度,以及他們所要的評量進程的指標。但我們不相信評量的技術,現在能讓我們說出服務一千名學生造成的X等級的影響,可以與服務四十五名藥物成癮的流浪漢所造成的Y等級影響相比。 到頭來,我們還是在找有用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會下價值判斷,說蚊帳比房子重要,我們會說:
與其思考要解決哪個議題,社會創業資助人在尋找稀有又強力的結合:他們想要資助有強烈使命感,而且有創業精神的領導人,並且有改革體制的想法以及可以快速成長、財務永續的堅定組織。這三個元素—人、想法、組織 (the person, idea, and organization)—在我們的訪談中,頻頻出現為選定資助計劃的主要標準。 [我們在尋找]一個組織,它的領導人在社會領域中的表現,必須要與在營利領域中的企業家一樣,對一個理想充滿熱忱,而且會嘗試把所有可能的資源用在建構該理想上面,不成功絕不罷休。 談到社會創業精神,你真正的重點其實就是社會創業家,一群有卓越創業能力的人… 這是一個掌握在一個人手裡的理想,你必須兩者都有。有一位真正的社會創業家,不表示他們就有理想,也不表示他們正處在一展長才的時刻。 在我們進行任何活動前,每個計劃都必須通過以下兩點的測試:1.這是不是個能改變體制的理想? 2.你的(巴西)柔術點 (ju jitsu point) 是甚麼(你的招式是什麼)?-你要用的槓桿點(手段)是什麼?它為什麼行的通? 觀點的不同,對於評鑑的角色來說有明顯的後果。很多基金會的評鑑方式,並沒有把抱持理想的那個人的領導能力、財務永續性、管理能力以及執行計畫的組織的成長率,或者是這個理想是否被其它地區採用等列入考量。簡短來說,就是很多一般的評鑑技巧,常常缺少了社會創業資助人所認為的成功的主要標準。 第二個關鍵的差異,就是社會創業能帶來快速、且有成本效益地普及社會效益的重要性。很多基金會在選定他們想幫助的議題及地區後,把自己視為透過示範性輔助金 (demonstration grants) 或小規模試驗計畫來測試新點子的角色。這些基金會針對特定目標以及一個假說,發展了一套變革理論或是邏輯模組;這個假說是關於哪些計畫或介入行動會對達成那些目標有幫助。那些計畫就會獲得補助金,而很多評鑑的技巧,都是用來評鑑那些計畫的成果:其進展是否符合目標,是否能證實基金會的變革理論等。一個成功的計畫,是否真的能傳播到其它地區、它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以及有無被其他資助人採用,這些一般都被認為是執行上的問題,它超出評鑑的範圍。 然而在社會創業裡,大規模的實施是主要的目標。成本效益、效率,還有與市場力量或經濟刺激的結合,都是評估快速成長潛力的關鍵要素。因此,社會創業中的評估,比較少測試實驗性的計畫或是證實變革理論,大多都是在追蹤一個介入行動或點子的成長或潛力。 我們的訪問也揭露了社會創業資助人與一般捐贈者處事的不同。社會創業資助人對補助金申請者,長期使用密集的審查程序。一般的資助人可能也有嚴格的挑選過程,但在更廣泛的慈善事業領域中,大家做嚴謹審查的程度都大大不同。一旦選中補助對象,社會創業資助人通常會承諾維持數年的資助,而且會與資助對象有極密切的工作關係,比其他不同處事風格的資助人還要更牢固。 被資助組織的成本效益及永續性、可能促進擴展的市場力量以及如收益及現金流等典型的財務指標,都受到密切注意。無形的目標也很重要,例如該創業家的個人成長、改變期待的理想的力量,以及社會創業家網絡溝通的價值。很多基金會把上述一些要素納入他們的慈善活動中,但在剛崛起的社會創業領域裡,這些要素在我們訪問的資助人中,幾乎全部都有出現。而正如下一節所討論的,這每一個要素都對評鑑的執行有重要的影響。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一直認為評估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認為有一個非常、非常嚴密的前端模型 (front-end model)是明智的。我百分百確信那是一個充分的績效評估模型。 基金會通常都會透過評鑑,來了解他們的補助所帶來的結果。無可避免地,成為被研究目標的介入行動,通常在接受補助時就開始運作,因此評鑑行動一定要同時或隨著補助資金的支出出現。選擇資助哪個補助申請計畫與其結果的評鑑,被視為兩個完全分開的過程。通常基金會在測試變革的理論時,它們的觀點是:「我們來試試新的做法,然後再評鑑看看它有沒有效。」 但對社會創業資助人來說,重要的是有強力組合,包括有對的人、一個足以改變體制的點子,還有一個可具規模的組織;而這幾個構成要素,通常都可以在補助案通過之前做事前評鑑。前期資助人較在意被補助人的長期表現紀錄;後期資助人比較注意點子的複製性或組織的力量。不管用哪個方式,社會創業資助人通常會相信他已經找到一個有實力的個人或計畫,在補助或投資之前,就有能力帶來正面的社會影響。在這個領域中,資助人比較傾向這樣說:「就來發現有用的東西吧!然後拓展它的影響範圍。」 這樣看來,在我們的訪問中一直被提到的「在決定資助前先評估」是有道理的。 接下來,還是需要評鑑基金會的資助及非財務的協助,是否真的幫助了該組織,或是理想是否有散播出去,以及如下面所討論的,理想是否經常受到密切的追蹤。然而介入行動有沒有效,是可以事先決定的,而這導致了我們在社會創業家的挑選過程中,所發現非常嚴謹的審查評估。 我們有非常嚴格的長期審查以及嚴謹調查程序。我們收到世界上來自七十個國家的申請案,而我們只資助了其中的百分之二…,〔我們的審查從一個〕非常長期的商業企劃書競賽開始。申請人在獲獎名單決定前,就先跟我們工作了六個月,我們主動與那些資深會員 (Fellows) 一起細部審視他們的企劃書、預算、他們規劃將來要工作的地區等。在他們還沒正式成為我們的夥伴之前,雙方熱烈的參與就已經開始了。 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該如何評量成效?它不但不會使社會創業家偏離軌道或分心,反而是社會創業家最能發揮影響力的一環。我們的解決辦法是盡可能地提前作業,這也就是為什麼挑選的過程是如此緊湊,其中包括五個步驟,每個步驟都特地獨立出來,並且根據我們那四個標準,進行評估及回應由這四個標準所衍生的問題。這確實能讓我們好好判斷申請人及其想法,看他是否真有可以創造改變的可能性。 我們很多的評估都提前作業。挑選的過程很緊湊。第一階段是創業計畫的過程,這一循環約有八到十個月之久。很多的績效指標都會拿來檢視,從何時要錄取下一個人、何時要拓展另一個辦公室、何時將有第一千位孩子受到幫助,到你如何辨別他們真的有受到良好幫助? 我們試著與這些人密切聯繫達幾個月甚或一年,帶他們進入我們的社群網絡,看他們是否符合我們的目標與理念、他們在這網絡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這個網絡人群喜不喜歡他們。 每筆預算都要有一個記敘說明,如:這是我想做的、這就是為什麼這會改變整個結構、這就是將會翻轉結構的策略等。在第一階段,我們只會問整體計畫的預算,不會一條一條來;到第二階段,就連你要複印的數量都會在意了。 「施瓦布社會創業基金會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這個範例也是我們一直在這個領域很多資助人身上,所找到的「事前評鑑up-front evaluation」。在為期六個月的評估項目,包括社會創業家的領導能力、社會影響的廣泛程度、他們點子的創新性 (innovativeness) 與擴展性 (scalability),以及他們組織的永續性等。而除了基金會成員外,候選人還分別由一名在社會創業主要領域中的專家(例如農村發展、微型金融等)、一名熟悉該地區的人,以及一名在社會創業領域中的領導人,做三階段的評審。 基金會成員會親自到能達到第三階段的候選人工作的地點實地訪察,而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去看看他們進行中的計畫,向當地政府了解這個計畫創造了多少工作?或有多少人受影響?醫療做得如何?收入有沒有提升?因為每項計劃性質都不同,所以我們沒有固定或最低標準。 不去現場訪視的話,我們一定會搞砸。若不實際去候選人那裡看看,然後慢慢來的話,那我們引進不合標準或無法融入我們社群網絡的人的機率,就高出百分之五十。我們至少一半的預算就那樣浪費掉了。有些社會創業家很會編故事,但到現場一看,卻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如果沒有去看看,那我們可能就被那種人騙了…我們真的很努力確定我們找到的是最好的。 施瓦布基金會的內部文件,對那些在訪問中不斷被重複提到的標準來說,是好用的核對清單。經過該基金會同意,他們的提名表、申請表、重新審核表都附在附錄A(略)。 至於社會創業的「事前評鑑 up-front evaluation」,與其他資助人在挑選過程的嚴謹調查,是否有相同作用,這個開放性問題,不是我們有限的研究能夠回答的。對那些關注有理想並單獨行動的新手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來說,事前很難預設什麼保證,說他們的介入行動真會成功達成目標。當然,要判定基金會的協助是否有用,預期分析 (prospective analysis) 還是不能取代事後評量 (after-the-fact assessment);不過它確實也反映出強調的重點不同;資助中、後期的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資助前比較傾向專注在現存專案的既有成果,資助後則較注意對規模擴展的評量。 譯員C:許庭瑋 (4,424字) 3.3 根據自訂目標比較進度 社會創業家通常知道衡量自我成就的最佳方式。 資助行動開始後,最常見的評鑑形式,就是依照資助人與社會創業家共同開發的一系列實際又針對計畫的目標追蹤進度。然而隨著情況演變,在雙方都表明同意改變方向的意願後,就算這個計劃沒有達成原訂目標,也會被視為是成功的。這需要資助人與社會創業家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這樣資助人才可以主觀的判斷,究竟改變方向是導致計畫失敗的證據,還是對未預見的情勢所做的成功適應。為了保持對社會影響規模,而不是影響類型的強調,一個實際上讓很多人受益的計畫,即使那些效益與原先設定的不一樣,很可能會被視為是成功的計畫。即使計畫很明顯的遇到難題,資助人的反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繼續支持社會創業家,其他可能會提出管理上的改變或理念的調整,而有些還會停止未來的資助。
我們與我們的資助對象非常緊密的合作。在資助任何計畫前,我們會看他們如何做績效評量;然後我們把他們收集的資料做摘要。在簽署補助金同意書前,我們可能會跟他們一起討論,然後問:「你們可不可以想辦法,把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項目放進評量?」,但我們仍然希望,績效評量不會讓他們感到太繁重。 一些受訪者指出,對執行評量績效的意願及執行上的複雜程度,似乎在社會創業領域中比更廣泛的非營利領域還要更大。事實上,對於績效評量的注重程度被認為是社會創業家的一個獨特標準。 影響評估對組織以及組織的建立方向對社會創業的重要性,使其有別於非營利組織,因為非營利領域可能就沒有〔如此明確地〕思考如何利用其他資助人的策略等等。 社會創業家完全專注在成果上。若為了更有效地達成他們要的成果,需要他們向某人報告,他們會的。 〔在非營利領域中,〕現今並不常使用〔績效評量〕。說真的,事實是非營利組織會找相對來說,他們可以簡單算計的東西,通常是可以讓他們表面上看起來好看的,然後會就此提報,而且一般來說,評量差不多就那樣打發了。 社會創業家有策略,他們有行動項目,測試過後,就回去把行不通的東西修改掉。他們對處理募款與預算方面,以及對資助人及董事會回報結果的方式,都很企業化。 然而,社會創業家投入的領域種類與地區非常廣泛,無可避免地產生了為單一計畫訂做的多樣化標準。我們訪問的一部分出資者,把自己限制在某個特定領域,像是教育,但大部分並不會這樣做。因此,他們大部分都無法對特定一組社會目標的進度方面,做整體的績效評量;他們的資助對象彼此之間,在產生相似成果的相對效益上,也無法比較。 要把兩個地方互相比較是很困難的-在不同地區,永續發展的策略會非常不同,而環境也很不同。 要掌握績效標準是很困難的,因為努力程度的社群針對性很強,〔而且〕也與大多數社會創業家服務的人口有關。若你在很沒落的社區工作,即使有一些小進步,也當成是一個里程碑,但這進步程度與傳統的標準一比,看起來就像沒有進步一樣,那該怎麼辦? 然而資助人也真的會仔細的追蹤社會創業家的進展,追蹤他們在關係開始時,與資助人一起設下的計畫及目標。我們發現所有受訪的資助者,都會拿資助對象的自設目標來評量其進展。 資助人說:「告訴我們,你為了管理那個計畫要評量什麼,而我們會要你為此負責。」 資深會員如何為計劃訂立指標,我們就為我們的成功訂立一樣的指標。一年兩次,他們會向我們報告他們曾說自己未來會達成什麼,以及他們真正達成了什麼。 [社會創業家]寫下自己的行動目標及里程碑。我們與他們一起努力,使他們進步,並使雙方都高興,不過評量是來自他們自己,我們扮演的是問責的角色。 若一個組織能建置一個好的內部回報系統,而那就是我們需要的…,我們試著幫助他們定義什麼是他們要達成的成果,要硬性成果 (hard outcomes,即量化成果 quantitative outcomes),也要軟性成果 (soft outcomes,即質性成果 qualitative outcomes)。我們相信做為資助人所要做的就是這樣,而我們不想引進另一個報告〔要求〕給他們。 為資助人及創業家在幾個月間的各項合作計畫發展績效評量的過程中,常常會形成一組有創意又實用的評量,而且對監視委員來說,是符合成本效益的,及時的,還會為社會創業家的工作社區客製化特定的成果。有時候,這需要資助人可能提供的大量財務投資資源,但通常標準都已經由社會創業家,在財務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收集好了。我們訪問過的受訪者,極為敬重社會創業家能發想出雖然不正式,但卻有意義的社會影響評量法: 他們有自己的方法以確定有沒有達到他們要的成果-就是詢問受惠人,他們通常對他們的成功有直覺,並且非常了解他們的領域。因此,他們可能會用非正式的評量,來了解目前成不成功。 一個好的組織若得到一些資源的話,就會自己創造出適用的標準,而這些是別的組織想不到的。例如: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當他們要想出消除貧窮 (poverty elimination)的方法時,他們就開始評量像是: 「你有沒有陶鍋?」 「你有沒有錫的屋頂?」 「你有沒有菜園?」 「你的小孩們在學嗎?」 「一年之中,有挨餓的日子嗎?」 他們在與窮人對話中,詢問他們怎樣才覺得人窮,並藉此想出十個問題,這真是太聰明了。 「閱讀室 Room to Read」組織試著藉由建立學校改善識字率。他們建好學校後就離開,不訓練老師、不注意孩子有沒有作功課或是測試家長的參與度,而他們也不是唯一影響識字率的因素,但他們評量的是像:「圖書館的借書率有增加嗎?我們去檢查的時候,那些書有沒有被弄髒或是不是有人使用?」或是「經過我們的幫助後,全國的識字率有改善嗎?」 關鍵的指標必須由你的使命決定,以我們來說,就是讓人們遠離貧窮。 這就是說讓人口袋裡有錢,我們的關鍵指標就是我們放了多少錢到人們的口袋裡,這還蠻容易判定的,我們可以相當準確的評量這項指標。 將每一個社會創業家與其計畫中的獨特目標相比,有兩個缺點,第一個是將它與更成熟的方法相比,看看新的想法有沒有比較有效時的困難度;第二是資助人無法聚集他們的整體進度成為任何單一的社會成果,然而他們能統計他們的資助對象中,分別達成各自目標中實質進度的百分比。 我們成功的指標是:在我們的投資中,百分之X達到他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我們資助的組織中,百分之九十要達成目標;時至今日,若我們回頭找投資我們的人,並讓他們了解也許有十二分之二達成他們的目標等級,那將會是相當的成就;而若我們可以在剩下的十家中,展示出其中的八家有好進度,那我們就樂翻了。
較少的補助數量但較多的參與,是了解你的組織有沒有做好工作的重要關鍵。你必須要親身參與,然後了解他們有沒有做的比以前好、有沒有比其他組織好,受惠人有沒有受益更多。 這也具有評估意義。光光是一年期補助案以及每季的進度報告的量,在大部分基金會中,相對於員工人數,代表著對已成立的補助案的嚴格檢查,如果沒有透過外部的顧問協助,是絕對辦不到的。然而在社會創業領域中,多年期的資金補助以及少量的補助案,允許基金會成員定期監視進度。在我們的訪問中,資助人表示:他們「只大略知道計畫活動」,就像一個創投投資人對他的投資組合了解的程度一般,在有如此頻繁的互動下,正式的報告及外部的評估人,常被認為是不必要的。 我們親自關心這些投資,所以只有特殊問題出現時,計分表才顯得重要。 我們每一季與各個資助對象會面,但非正式的會面部分,可是多的多了。 我們要求最少每三個月回報狀況。若他們怠忽職守,我們就開始緊迫盯人,通常現在的狀況是有什麼風吹草動了,他們就會立刻讓我們知道,因為他們很興奮。 我們不用表格來報告,他們不用填表格。 這種高度參與的另一個好處,是資助人能給社會創業家的建議與援助。 無疑的〔社會創業家〕需要為一個高度參與的關係做好準備。要找到有用的想法好難,而要找到了解如何建立公司的社會創業家也很難。他們面對好多困難,所以你一定要跳下去跟他們一起努力。也許有一些組織是你可以比較放手不管的,但我還沒見過那種組織。
我想績效評估最深切的幾個問題,將會是評價導向的 (judgment-based)。我發現社會創業家在改變路線並自我修正上,有很了不起的能力。有人花了五年時間使用同一策略,然後突然在一個開車上班的早晨,他們明白自己被那個方法拘束住了,於是召集他們的高層人員,並說他們很認真的考慮策略上的改變。 你必須要教會投資組合經理人,有些時候是必須要改變里程碑的。只因為一個人沒有達到里程碑,並不代表他是輸家。這較接近藝術而不是科學。 我們的「觀察名單watch list」上有兩個投資:當管理團隊沒有展現出達成目標的力量或是不知道為何他們做不到時,我們必須問自己:「他們有那個能力嗎?」。然後我們分析給他們看,並承諾會與他們一起努力,讓他們往前進入下個階段。我們看到其中一個投資的管理團隊,對問題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並且也大大改變解決的方法。 對於改變方向的預期很容易被接受,所以「綠色迴響Echoing Green」基金會在年度報告時,固定會詢問它的資深會員: 你的計畫重點或組織使命有改變嗎?若有,它如何改變?為什麼會改變? 重新檢視你的計畫邏輯模型: 。自從創造出這個模型後,你改變了什麼活動、優先事項或目標? 。為什麼改變?
有些我們資助的組織,就是沒辦法如他們所想的一樣有起色,而我們也討論過如「你什麼時候要喊停?」「它什麼時候會變得不值得?」但是我們從不因為計畫不順利而停止資助。我們會資助三年,但最多如此。我曾遭遇過一些問題,使我可能不會恢復資助,但是我們解決了那個問題,那就像婚姻一樣。 我們真的很努力的創造一種印象,就是我們是朋友;而且一旦你被選上後,完全不用擔心我們。我們從不讓你失望、就算你失敗了,也不會忘記你;因為我們選擇了你,所以你的失敗就是我們的失敗。 其他資助人,特別是用債務及股權方式投資而不是用補助款的資助人,對於挫折的容忍限度少很多。身為投資人,他們在尋找財務上及社會上的收益,所以失敗會帶來額外的後果。做投資的人與做資助的人之間觀念的不同,就是在廣泛的非營利領域中,對「無績效nonperformance」表現更大的容忍-這種態度令人驚訝的是,在社會創業中幾乎一樣的普遍。就如有些受訪者指出,這種態度也可以對增強成效造成阻礙。 [非營利領域]的文化是說所有的事物都是成功的。但在我們到達一個境地,當我們〔可以承認一個組織〕在目前的管理下是不可能規模化之前,我們不會看到規模化的組織。 我們的作為聽起來殘酷…每六個月強迫做排名,並檢視我們所有的投資-從不會超過二十個。我們從各個項目檢視並為它們排名,沒有平手這事。第一次我們有一些一心只想保住自己飯碗的人,現在我們是一個團隊。若一位投資經理人的計畫一直都是墊底的,那這就暗示. . . 我們所犯的其中一個錯誤,是我們太講究把每件事都做成功。我們放太多的能量在輸家上。所以我們需要把能量放在贏家上,但有很大潛力的輸家也可以。每個月,投資經理人會比對進度與目標里程. . .,若我們發現不祥之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Mene, Mene, Tekel, Upharsin,出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第五章第25節),就會立刻採取行動,以減少損失。 譯員D:許庭瑋 (4,935字) 3.4 追蹤組織的發展與成長階段 目前許多評鑑方法的缺點是,他們使用的是專案評鑑 (programmatic evaluations),而非組織健全評量 (organizational measures of health)。 雖然社會成果可能大不相同,但組織發展的階段以及影響規模的簡單評量-像是受正面影響的人數-可以適用於整個投資組合。然而評量的方式,會隨著社會創業家的組織的週期階段不同,也會被資助人對於創業家的強調程度、組織的永續性或是理念的複製所影響。 A. 週期階段:我們的受訪者都傾向專長於社會創業家創業週期的不同階段,而他們的評量在不同的階段,也強調不同的要素。 組織在不同週期階段會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想要在草創階段、初期成長、中期發展,一路到底都參與的資助人太天真了;創投公司較傾向專長於某單一階段-生命週期的其中某一階段。 將注意力集中在最早階段的資助人,並不指望社會創業家有成本效益或是帶來發展健全的理想,因此他們會不太願意在這麼早期,放太大的權重在成果效率的評量或是影響程度上。 品質評量的類型,依組織的生命階段以及發展程度而定。 我們會被任何嘗試要標準化評量的系統冠上負面的偏見,因為若你把一個在初期階段努力建立體制變革基本架構的社會創業家,與只是在設計小零件的人相比,社會創業家會讓人感覺非常沒有效率而且花錢。 我們會基於組織的年齡來評量他們服務過的人數-我們會預期較年輕的組織服務的人數會較少。 若〔該組織〕有十年歷史,那他們應該要達成某種程度的效率。 對組織的期待會隨著時間改變,對社會創業家這個角色的態度亦然。在此我們的訪問顯示了有兩種不同的資助人,一種是把社會創業家視為他們的主要援助目標,另一種是開始把他們的重心轉移到組織的成長或是生命週期後期的理念散播情形。著重在創業家的那些資助人,就算創業家離開了組織也會持續支持她,而他們通常會把個人成長也納入評量要素裡。 我們已經在社會創業家身上放了重本;他們就是變革的驅動者。個人是能夠建立組織的關鍵;我們並不把眼光放在組織上,我們資助的是創業家。 〔一開始我們想:〕「若社會創業家已經不在其組織工作了,那就應該剔除他們」。但我們想這沒有道理,因為他們通常是連續性社會創業家,並且有時候會在組織間移動。我們需要集中在個人上。我們不是一個組織的社群。我們是社會創業家的社群。 綠色迴響 (Echoing Green) 的半年度報告提到: 準備一個專業的發展計畫,以確保你成為有效率的非營利領導人也是很重要的事。請至少敘述一個你為個人成長所設的目標,以及至少一個為專業成長所設的目標。 另一個情況是,資助人談到一個明顯的重心轉移,從支持創業家個人,變成支持組織後期建立規模、重視效率及永續性;例如創投投資人,他們尋找一支強力的團隊,而不是個人的社會創業家。這些資助人提到找出「優秀的二號人物」當作營運總長的重要性。 投資人才容易依靠有商業頭腦及社會手腕的創立人,我想這個觀念是正向的,但我又想這個觀念式微了,你需要的是專注在組織及領域上。 最大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從社會創業家身上看到,那種從家庭導向的新創事業變成真正的機構而該有的開放態度? 」,其他的全都是好的小指標〔但是較不重要〕。 我們不是在評量社會創業家,而是社會創業組織。對我們來說,這是關於發展使組織文化永續經營的系統一事。 我們不只必須找出好的社會創業家,也必須找出好的「二號人物number twos」,可以在組織中幫助建立發展。我想需要有相關書籍或研究領域是關於如何成為好的營運長 (Chief Operating Officer),他們是不被歌頌的英雄,但他們是整幅拼圖中關鍵的一塊組片。 那些認為有需要從評量個人成就轉為評量組織成功的那一群資助人,很憂心如何在社會創業家將領導權轉移給繼任者後,對個人與組織所造成的後果,找出處理的最佳辦法。 隨著組織成長,我們並沒有給那些已經不適任管理組織的社會創業家一個優雅下台的機制。我們必須要找出讓他們感到光榮又能讓他們好好離開的方法,就像商業中的金色降落傘 (golden parachute,優渥的離職補償),但我們沒有任何可以處理的機制,而且若我們不正視這問題,組織就不會真的規模化。 B. 組織發展的評量:在特別注重組織發展的資助人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強烈的趨勢,就是強調透過受惠人所接收的最終影響,來評量組織的能力及成長。這與最近慈善領域強調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的運動雷同。 我想你必須先想清楚社會效益的第一要務,第二要務等等。舉例來說,也許你想要藉健康技術轉移,用蚊帳斷絕瘧疾的話: 。第一要務就是要進口機器、準備工作做好,然後先做出三百個成品。 。第二要務則是行銷以及將蚊帳發放給窮人的系統,製造N個工作機會,開始改變蚊帳工業的運作。 。第三要務-我們到目前連碰都沒碰過的-又怎樣?你有做過任何影響瘧疾傳染媒介的事嗎?對我們來說,若你能把第一跟第二步做好,我們就已經將這個領域往前推動一大步了。除非有人願意支付這些費用,不然我們不會追縱後續效益。我們為了永續經營,可不能為那種學術研究花錢。 通常,對成功的主要評量,僅僅就是成長率,不論是在資金募集、員工人數或是受正面影響人口等方面,而沒有鑽研那些人們所受的影響本質;舉例來說,「阿修卡(又譯:阿育王)Ashoka」組織,定期的對其資深會員 (Fellows) 進行調查,要求他們比較現在與自身組織五到十年前的情況,對預算、員工數量以及辦事處的數量等進行比較,問卷中也包含了以下問題: 在你當選「Ashoka資深會員」之時,大約有多少的個人、村莊、生態系統等等,受到你努力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中還有多少影響是現在還持續存在的? 雖然社會影響的類型幾乎完全不同,但通常整個投資組合的成長評量會被合併計算: 我們包含收入及影響的投資成長率有41%。受影響人口數是我們目前唯一用來評量影響的指標;之後,我們評量各個組織的品質部分。 「敏銳Acumen」基金會在對投資者的報告中寫到: 我們的努力已經影響了超過50萬人,包括改善生活的醫療科技的派發、現在擁有自己房子的人、藉由微型貸款做起小生意的婦女、靠新的灌溉技術增加收入的小農,以及經由我們投資計畫所創造出的工作機會…自從我們的投資開始,已經製造並送到低收入家庭手裡250,000頂耐用的防瘧蚊蚊帳,9,000個氟化物過濾器,還有3,885 套滴灌系統。 我們訪問的其他資助人對組織發展採取不同的評量方式,他們跳脫重視受正面影響的人數及花費多少錢的作法,改為專注在隨著組織成長後,必須要達到的不同成熟階段,雖然追求的社會成果不同,但這幾個成熟階段是相似的。 我們對於發展中組織的能力尤其感興趣,並觀察那會導致什麼影響-我們想知道,建立組織能力後,他們確實有增加影響力。我們把影響視為副產品,而不是絕對度量 (absolute measure)。 在他們的議題領域與計畫裡,績效評量有所不同。但在組織能力裡,我們所有的受資助人都很相似: 。董事發展 。資金籌募 。員工發展 。公共關係 能力評量就標準而言是很類似,但是就目標而言卻不相似:全球的衛生組織與給女孩的領導訓練計畫兩者相比,在員工需求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 綠色迴響基金會要求它的資深會員,在為期三年的補助期間,每六個月要提報簡潔但是完整的進度報告。報告要求回答各種社會創業家進度的細節問題,包括一系列關於組織發展的問題。舉例來說,半年度報告問了: 。你的基礎建設如何演變,以支援組織的需求? 。你是否有支持你將來成長計畫的資源到位? 。若你目前還沒有能力支持自己計畫中的成長,請形容你如何找出並培養未來將成為你組織成功的重要人員的規劃,這些人包括董事會、顧問(專業的顧問小組、非正式的專業資源或是專業導師)、員工及志工。 。你是否已經取得為了提供服務所需的實體資源 (physical resources)(例如:辦公空間、電腦、會議室等)?這些資源是否足以支撐到年底或是你會找尋擴大規模的能力嗎? 經過綠色迴響組織的同意,半年度及年終的報告都收錄在附錄B(略)。 另一個定期評量組織績效的工具,就是平衡評分表 (Balanced Scorecard);「新盈利New Profit Inc. (NPI)」修訂了這項工具,以供社會企業使用,並且用它來監測旗下社會創業家的進度。平衡評分表有明顯的優勢,那就是能把多種績效評量放入單一架構,並能每季追蹤。這對讓管理人隨時注意必要的不同面向,以確保組織能確實地與其策略緊密結合方面尤其有幫助。因此,它結合了大量不同的評量方式,這也是在這份報告中一直討論到的。 NPI所使用的平衡評分表包含五大類別:社會影響、客戶及主要利害關係人的滿意度、內部營運流程、學習與成長以及財務收益。雖然它整合了這些類別的報告,但平衡評分表並不會詳細說明各種類別中應該收集的資料,也不會加強分析深度。舉例來看,在社會影響中,組織一般來說,會選擇在第二章提到的自己決定的進度評量,並以此用來回報自己所完成的影響。資助人因此可以記述那些達成他們平衡評分表目標的受資助人百分比,但並不見得比較能夠彙總社會影響或收益;一段NPI平衡評分表用法的簡短描述收入在附錄C(略)。 C. 理念的複製:其他資助人著重透過宣揚理念以及組織的發展來提升影響。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可能本身是具有永續性的,就算一開始引進方法的組織自己不持續經營,該理念也可能散佈出去;舉例來說,Ashoka組織在資深會員被選入組織後,每隔幾年會對他們進行問卷調查。 每年我們會對進入第五及第十年的資深會員進行問卷調查;這是自願性的,不過約有70%會參與。這並不是要評量社會創業家,而是問問他們「你的理念已經有被他人複製 (independent repetition) 了嗎?」「它有造成你政策上的改變嗎?」 我們混合使用量化評量及質性評量-並且發展出對加入五或十年的資深會員的個案調查,就如同問卷調查一般;每年的個案調查數量不同,但是每年不會超過十到十五個。 除了一連串關於組織成長的問題及Ashoka支持的價值外,該問卷調查包含了第三個部分,特別著重在理念的傳播,提問: 請提供你的理念/計畫由其他獨立組織(非你所經營)、企業或是政府,所複製使用的據點數量。 其他問題詢問對於政策及立法的影響,以及接受過的媒體報導或獎項。然而Ashoka一般來說,不會各別驗證那些它的資深會員自我報告裡,提到的影響及收到的表彰。 經過Ashoka同意,一份Ashoka針對其資深會員的十年期問卷調查的副本收錄在附錄D(略)。 譯員E:許庭瑋 (3,908字) 3.5 估計經濟效益 (Economic Benefits) 及財務槓桿 (Financial Leverage) 我們無法以金錢以外的形式追蹤社區影響程度。 一個較複雜卻得以追蹤具有不同社會目標的組織的社會效益,就是觀察各種不同的經濟績效 (economic performance) 評量方法。社會創業資助人因為他們的商業性傾向,所以很強烈地想要把每一筆投資的慈善捐款所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最大化。正如先前提到的,他們選擇計畫的原則,較多原因是基於預期造成的影響,而不是對某些善因有所偏好。這樣對經濟槓桿 (economic leverage) 的強調,可能會演進到社會創業領域評估的獨特特性裡。 我們的訪問揭露了三個評量社會創業計劃經濟績效的方法:分別是「傳統財務績效標準」、「由社會創業家活動所產生的金錢價值估算」,以及「從其他資源募款的手段」。 A. 傳統財務績效標準:財務績效的傳統評量,被視為是組織永續性及管理團隊實力的好指標。在販賣產品或服務的社會創業方面,它也可以做為需求的指標,並且也許能反映受惠人對這些社會效益的重視程度。 一個基本、穩健的財務會計系統是這個領域實務者所從事的核心,那是需要被評量的前半部分。有時候這與社會目標有直接相關。若我們為盲人製造一樣產品並且平實標價,讓每個人都買得起,並且我們還可以收支平衡,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顧客是所有我們要做的事情的原動力。我們滿足了一個需求,因為如果我們做的很爛,那他們就不會來找我們。 傳統財務標準也揭露了該事業運作的經濟模式,同時支持以更大規模的拓展及提供服務或產品所需資本的預測。而當市場力量與財務標準密切結合-也就是說若該社會效益能增加受惠人的收入,並且也可以讓該社會創業家的組織獲利-資助人看到的是眼前高槓桿效應以及快速拓展的機會。相反地,若該計畫大量依靠慈善補助金,而且造成的效益也很模糊,這樣的話有些資助人就會不願投資。 所有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著眼於經濟模式的優點,但對營利投資或使用債務及股權投資,而不是傳統資助或津貼的資助人來說,是尤其重要。顯而易見地,若慈善款項能創造社會效益,並且仍能透過真正的投資獲利「回收」,那它就是個比起單行道般的長期捐獻,還要更強力、更有永續性的經濟模式。特別是在與這些資助人的訪問中顯示,他們強調追蹤財務績效的傳統評量,以做為對所投資公司的評估方式。 我們是債務投資人,所以我們投注了很大量的資金在永續企業上;對我來說,有一部分是基於能夠透過營運產生盈餘。 若我們證明能達成成果,並且有系統性地產生變革,而且我們投資在社會創業家身上的錢90%能回收,並重新投資在新專案上,那麼我們就主張這可能是你支配慈善款項較好的方法之一。 B. 估算社會效益創造的貨幣價值 (monetary value) 有些社會創業家邁出更重大的一步,試著估算他們創造出來的社會效益之貨幣價值。這個估算就可以與所需的慈善資源做比較,並讓他們的資助人了解自己的投資於理論上的「社會報酬」。很明顯,有些種類的社會企業,例如致力於減少貧窮、住宅、公平交易認證,以及其他主要的經濟效益的社會企業,會比專注在像是保存生物多樣性或推廣公民參與這樣議題的組織,還要來的容易貨幣化他們的社會影響。當一個組織能夠輕易給予它賦予的社會效益作評價,這個計算是一個能夠評估這個社會影響的成本效益的方法,並且能與其它的投資相比較。一般來說,犯罪、貧窮、藥物濫用以及醫療保健所帶來的大量社會成本,代表了社會企業將會時常表現出正面的經濟價值。(見REDF:計算投資的社會報酬) 舉例來說,ApproTEC組織,設計並販售手動的灌溉幫浦,給在肯亞及坦尚尼亞的基層農民。藉由小心追蹤他們的裝備以及親自拜訪農場,ApproTEC由那些幫浦的實際運用而得以收入大量增加。經過計算,ApproTEC估計,其商業活動產生了每年三千七百萬美元的新獲利及工資,肯亞的年度國內生產毛額(GDP) 因此增加了0.5%,坦尚尼亞也有0.25%。年度預算有一百八十萬的ApproTEC組織,計算出他們收到的每一美元捐獻,能產生二十美元的經濟效益。這些農夫們收入的增加,可能帶來很多其他的社會效益,包括:疾病的減少、更好的房屋、教育資源的增加、公民參與的進步,以及非洲中產階級的成長等。這些成果部分有持續追蹤發展,但只有經濟效益有計算。 這個評量方法的好處是,資助人可以很容易地合計他們所有投資的收益,提供整體表現的某種評量。然而這種社會報酬,非常不同於債務及股權投資人可能獲得的真正財務報酬-不論它創造出了多少社會價值,沒有任何機制能收復及回收那些社會價值,並變成未來的現金捐獻的來源。 此外,因為了解這種方法在評價非貨幣效益 (non-monetary benefits) 的嚴重限制-有時可以說是整個計畫的重點-我們訪問的資助人中,沒有一個是把這個方法當作唯一選擇要資助哪個計畫,或報告他們援助計畫及投資整體表現的唯一評等標準。 C. 利用其它資源籌募資金 第三個估算多樣的社會創業家投資組合的經濟績效的方法,就是看看該創業家能否從其他的資源取得額外的基金。透過相對補助金 (matching grants) 或非正式的合作來運用基金,在慈善事業裡是稀鬆平常的事,這還被稱讚為成功的方法。然而除了相對補助金以外,計算實際的運用情形,通常並不是正式計畫評量的一般要素。 槓桿效應並不會顯示該經濟模式的優點,也不會顯示出所達成的社會影響;但是它確實令人聯想到,該組織成功地向其他資助人展示它的價值,並且拓展它活動的規模。最重要的是,讓人覺得該組織,就算在資助人的財務支援結束之後,也能繼續它的運作與永續經營。 我們自從創立開始到現在,已經投資了兩千萬美元,我們做了一個不嚴密但符合方法邏輯的研究,目的是要看看我們的創業家,後續從別的資源獲得了多少資金。我們粗略計算出創業家在別的資源中,取得了額外的九億四千萬美元資金,這給了我們一個44比1的投資社會報酬2。 我們帶來了什麼價值?這代表了我們所造成影響的金額。我們已經可以追蹤到有兩千五百萬的新資金流向我們的投資;若我們的資助對象中,有人得到大額的補助金,那我們可能就是幕後的功臣。 在有些情況下,資助人可以實際的追蹤到,那些因為他們的直接參與而得到的補助金。其他情況下,他們只能估計所收到的募資收益,是因為受到例如獲選Ashoka資深會員,或受邀到達沃斯 (Davos) 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參加演講討論的光環。大部分的資助人並不會嘗試確定,哪些資金是他們的援助帶來的直接成果,也不會主張他們達成的槓桿效應,能轉化成任何特定程度的社會效益。然而,他們確實認為自己在發掘並支援一些還在初期階段的組織方面,有一定的功勞;而那些組織後來都已經成功地達成重大募資,並且擴大規模營運。 簡短來說,這些經濟績效的評量法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的。從很多方面來看,它們只是那些社會創業家組織的成長與發展的計量指標。它們揭示社會創業家做法的優點及潛力,確認她有發展一個永續組織的能力,並且確認資助人有正確挑選「贏家」的能耐。它們提供資助人一個好方法,能思考他們做出的選擇,但它們並沒有證明,哪個特定方式最有效或是最符合一筆捐款的普世價值 (universal value)。慈善績效評量能濃縮成一個單一數字,並能在不同目標間相互比較的這個希望,對社會創業領域來說仍然是個很大的誘惑,但我們所有的受訪者都不相信,這些經濟績效評量能達成那個目標。 3.6分享學習 當你將社會創業家聚集在一起時,他們會開始從彼此的工作中學習,並將之轉變為非常高效能的方法… 社會創業資助人逐漸開始重視,在他們旗下的創業家與他們自己之間那些來自於支援、學習與合作所帶來的價值。我們發現一個一致的現象,就是強調:透過社群網絡的發展學習、受資助人對於資助人提供非貨幣援助之品質的回應,以及透過故事與趣聞軼事的方式分享經驗。與其用書面報告或學術研究當作獲取知識的手段,社會創業家還是比較喜歡直接的人際互動。 A. 建立人際網絡:所有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認為在社會創業家們間建立與維持社群網絡是他們使命的核心,所以這也是他們需要追蹤與評量的事項。 〔我們想〕組成一個社群,並把世界頂尖的社會創業家們聚集在一起,因為社會創業家們是孤單的,他們彼此認同,然後開創了一個團結組織… 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找出社會創業家,並支援他們,但我們的第二目標是建立一個效能大於結合各成員的社企社群 (more than sum of its parts...,意:1+1>2) 他們都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不論他們身在何處,我們一年讓他們正式的相聚一次。此外我們會在一些話題上做即席會議。若我發覺有三到四個人在個別募資方面遇到瓶頸,而我知道有人很在行,那我會把他們都聚集起來, 他們很容易就建立起人際關係,並自在的相互交談。他們在不同的領域發展,所以彼此不是競爭者。他們會有像這樣的對話:「我知道這個資助人,正在找教育領域中需要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你何不去申請看看?」 雖然所有的受訪者都了解人際網絡的益處,但有一些社會創業家發現這種聚會非常花時間。當人際網絡能帶來實際益處時,例如在達沃斯 (Davos),與世界最大企業的總裁們會面時的募資潛力,像這樣的益處就比旨在社會創業家們互相學習、援助的集會還要來的有益許多。由於此領域現今的規模仍小,由不同組織資助的社會創業家有很多重疊,很多Ashoka資深會員、也是Schwab資深會員、Echoing Green資深會員、AVINA領導人或是Skoll得獎人;雖然他們可能是在不同階段受個別基金會資助,他們經常被期望要在各個網絡中保持活躍。在這個小世界中,為了要培養自己社群裡的受資助人,或是與他們建立合夥關係,各個資助人善意的努力是可以在不經意間累積的。一位社會創業家這樣講道: 我們有六個主要資助人,每一個要求至少一個星期的會談,突然間你們佔去我七個星期的時間。沒錯,人際網絡是很重要,但我們真的需要把時間花在以下兩件事上面:管理與募資。若網絡社交能轉變成金錢的話,那很棒。與其他社會創業家交談,非常有價值,我可以叫出六個曾經對我非常有幫助的社會創業家的名字,但一年中我究竟真正需要做幾次這樣的會談? 另一個資助者常犯的錯誤,是自認讓自己與別人成為夥伴是有用的事,但實際上並不完全是,尤其是在資助者要求下達成時。有多少夥伴公司是因外部強迫而成功的?確實是有,但只有真的符合策略與使命緊急 (mission critical) 時刻才成立。 既然建立社群對大部分資助人來說,是有重要附加價值的活動,他們大都會追蹤一些他們培養參與及合作的簡單指標。這又是另一個一般基金會不會列入評量的要素了。 我們以有多少〔我們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一起努力這一點來評量。我們看到它漸漸壯大起來,我們有創業家們的回饋-他們所說的真是太棒了,真的很感人-我敢講我們所做過最大的貢獻中,建立這個社群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們相互合作的方式,對〔他們所有人〕及對他們服務的對象來說,都有極大益處。 B. 受資助人對非貨幣性支援 (non-monetary support) 的回應:除了建立人際網絡之外,大部份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誠心的希望提供有意義的非貨幣性援助給他們所資助的社會創業家。因此,他們一部分的評量活動,就包括了追蹤評量他們自己的效率。 你必需評量自己提供的技術支援的價值… 我們利用第三方對我們的社會創業家進行調查,看看我們的表現如何,例如像是我們與該組織的指導會議 (coaching meetings) 之類的問題。 Ashoka並不常評量單一資深會員的表現,而是它對這些資深會員的表現。舉例來說,成為資深會員對該會員有哪種程度的幫助等;這些東西對於決定Ashoka的價值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評量自己做得如何,最主要的是為了自己,以當作讓我們改變或改進自己行事的回饋機制。這是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第一個原因,我們為了自己的計畫而做,把它匯集成一個學術領域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為了每位我們的社會創業家,我們問問自己:「倘若我們不存在,他們今日會在是何種景象?」,「我們的存在為他們做了什麼,使他們有重大的變化?」。我們懇求他們對此問題的回饋,而大部分都回答的很好,對我們而言,這是我們成功的指標。 C. 說故事:我們所有的受訪者無一例外的,不是補充他們更精細的評量細節,就是大量透過故事或趣聞軼事的方式,以形容自己的特別成就。引人入勝的故事是慈善事業中慣用的技巧,而這些故事的可靠性,通常不足以成為形塑社會影響明確結論的基礎;然而它們能啟發新的捐贈者、為共同的問題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法,以及抓住成功的無形要素-每一樣都非常吻合社會創業的文化。事實上有些受訪者還深信,其他的方式並不能完全的紀錄社會創業家的成就。 在社會創業領域中,要評量是很困難的,而把握那些故事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很複雜。 不像傳統受補助金資助的計畫,可以間斷地進行,並且可以作回顧性評量;社會創業家總是處在他們過去實際的成就以及描繪他們未來的雄心遠見的中間。他們的成功,一部份總是依靠一些微妙之處,例如理想背後的衝勁、大眾態度中變革的徵兆,以及主流機構及政府,以令人苦惱的速度接受他們的理想與計畫。受訪者們發現他們很難想像,更正式的評量技巧能夠捕捉到對影響散播這麼重要的微小差異。通常,我們發現那些「故事」,並不是在重溫那些感人的時刻,而是對非常實際成就的開放式報告,例如受到聯合國或當地政府的肯定,這種不能用其他方式量化或追蹤的成就。 會在影響評估上表現非常差的人之一,就是在匈牙利為失能人士服務的女士。若你量化影響人們生活的金錢成本,那麼她只影響了600人。這個人數比一些單一的公立(收容)機構的人數還要少,所以她不會有很高的影響力。但她想要改變一般人對於一位失能人士在她的世界裡能做什麼的想法。改變人們對失能人士的預期心理,本身就是很大的影響。她的組織改變了在匈牙利國會的立法,你要怎麼量化它? 這個團體聚集了一個聯盟,促使了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法案 (American Disabilities Act) 通過立法;以前從沒人聽說過這個團體,但他們把辯論的重點從失能轉移到人權上…我不認為你可以把它們放到表格上,讓它們看起來有很傑出的成就;我想這代表的只是一個懂得運用策略的小團體的堅韌。 也許我最驕傲的成就,就是由於我們的努力,孟加拉政府正在立一個新法,要求雇有十個以上,介於生育年齡女人的工作場所,需設有托育中心。 改善生活是攸關「品質」的事,我們必須從品質上捕捉故事中的精隨,看社會創業家是如何做出那些平價的東西,並將之銷售出去。ApproTEC是如何在留意自己的影響上做得那麼好的?他們讓零售店的老闆幫助不識字的農民填寫一年的保固單,這樣他們就知道每個產品在何處。〔學到這些經驗與量化他們的經濟效益不同。〕把握住這些方法,並將之轉移到其他組織是很重要的... 譯員F:許庭瑋 (5,576字)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讓人們離開評量這個話題,而重視管理這個主題。它們之間的差別,並不細微… 社會創業領域為基金會及私人慈善組織的角色,帶來一個新穎與特別的遠景,而這個從根本上就不同的觀點,影響了評量的目的與實施。社會創業資助人引進企業化的心態,若可以從垂手可得的資料與個人經驗推論到的話,他們會很滿意介入行動的效率。他們強調的就是把理念付諸行動,並且盡可能越快、範圍越廣越好,同時為他們提供的資金,取得最大的槓桿效應。他們認為資訊與評量只有能及時並有效的分辨出好機會、增加影響的規模或是協助他們的受資助人時,才是非常有價值的。若評量的結果沒有被採用,那一開始根本就連收集都不需要。 若你確實執行了一個評量系統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改進行動,人們就會覺得這一點都不值得。但若你在那個方向做越多努力,那麼就越有可能會值得。 其中一個受訪者形容了在社會創業中,理想的績效評量系統:
5. 它必須有及時性才能有實質作用-做決定時,必須有正確的資訊在手上。 可以確定的是,社會創業中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若各個基金會能夠為散佈並執行他們成功引領的理念多負一點責任的話,它們可能會大幅的增加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畢竟長久以來建立的一個觀念,也就是基金會提出新的方法,好讓政府大規模執行,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幾十年了。有時其他資助人會複製或是又提出新的示範計畫;但好想法經常都可能無人過問,永遠碰觸不到他們原本可以幫助的那些人。 很多昂貴的評量背後的學術嚴謹層級是很令人欽佩的,但太耗時是它的致命傷。這證明了一個介入行動,即使此時此地有用,不代表它多年後,在不同的情形下,還能夠發揮相同功效。相信一個計畫有能提供立即幫助的第一手知識,也許足夠證明它值得資助,而更快速的資助,可能更快地幫助更多生命。得知五十萬人有了更好的生活-不論是何種形式、程度-對有實效的慈善事業 (effective philanthropy) 來說,最後可能也比驗證那些從來沒有被大規模複製的變革理論假說,還要來的重要。 在挑選及支援社會創業家時的嚴謹、合作及高度參與的程度,似乎也有優點,而員工與受資助人的比率,也比大部分基金會高。在營利投資中,為了社會變革而使用債務與股權投資做為手段,除了提供補助給非營利組織的年收入外,開啟了使用基金會捐贈基金 (endowments) 的可能性。最後,有一個重要的認知是,一個組織的經濟與管理對於它長期的計劃性影響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此領域的一些基金會,已經開始與他們的受資助人作進一步的參與,更加注意能力的建立,及更多不受限制的營運支援。 然而社會創業領域的資助人,也能從其它評量方法受益良多。幾乎大家都依賴的無外部核實的受資助人自行報告,雖然快速又便宜,但大大的減少了結論的可信度。在不相干的領域與多樣的地區中工作的趨勢,嚴重的限制了專業的深度,而這個深度在對受資助人的挑選與支援上,原本可以派上用場。沒有清楚與專注的計畫目標,大部分的社會創業資助人無法組合出一個協調的計畫,來處理一個複雜社會問題的多個層面,亦或是追蹤完成任何更大的目標的整體進度。但他們投資組合裡的補助,不論各自有多具影響力,通常彼此都沒有相關,所以無法創造出1+1>2的綜效。 總之,沒有更加嚴謹的研究,你沒辦法知道一個剛剛發現的新想法,實際上對遇到的問題來說,比以前可能試過的任何方法都來的有效。收集所需的實際資訊,對立即的管理決定來說,是很重要的,但對那項知識的彙編 (codification) 也很重要,這樣才能發現更多的通則,學習也可以更廣泛的分享。若結果沒有持續地及有系統地追蹤的話,要隨著時間進步會非常困難。 在很多方面,非營利領域目前的階段,就像以前法人組織五十年前的世界一樣,那是在由學者、顧問公司與實踐者們發展出來,造就普遍提高生產力的管理、效率及策略原則之前的世界。即使是在如此有限的評量研究內,我們還是清楚地了解到,在社會創業領域中,充滿了獨立發展出自己一套方法的個人,但他們的經驗還沒有結合成令後人獲益的一致性知識體系。我們希望這份報告,能代表大家正在朝那個方向努力的開端。我們的研究參考了相關文獻,並對資助人、社會創業家及該領域的學者們進行一系列共24次訪談。我們的研究內容並不廣泛,也沒有給為社會變革募款所帶來的各種存在已久的評量挑戰提供現成解答。任何試圖將現今各基金會在慈善事業及評估使用的方法作概括的行為(更別提對社會創業的諸多不同定義),都會冒過度簡化的風險,然而,我們希望這個報告收集的綜合議題及範例,可以刺激更有建設性的想法、對話與合作。
但在社會創業的領域中,這些都是成功的核心標準。被認定為社會創業家的人都是社會變革 (social change) 的擁護者,因此他們身為領袖的個人成長與能力都會被用放大鏡檢視。快速成長並且能持續經營的組織(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都是傳播社會變革的工具,所以他們的財務健全以及資源利用的能力都會被檢視。最後,擁有創新的方法就是社會創業家的一個決定性的特性,而那種方法在其它組織或地區散佈的廣泛程度就是成功的主要標準。只要他們的補助對象 (grantee) 確實善用可持續的手段,快速提供大規模社會福利,那些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似乎不會特別在乎受捐贈組織對專門處理的特定社會問題的選擇,也不會特別關心他們工作的地區或是他們造成的社會成果的種類。
總歸來說,在社會創業領域中的評估,與慈善事業中的評估是相似的,但也反映出明顯的態度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一部份是根植在評估慈善事業的學術淵源以及社會創業領域中的創投資金影響的分歧所致;簡單來說,就是學者跟商人測試點子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 成功的基金會常常會發展一套變革的理論或是邏輯模型,接著資助示範用的計畫,並使用評估來測試或是改進他們的模型。若是這種介入模式成功的話,他們通常會將大規模推行的角色交給他人;然而在社會創業領域裡,主要的目標是盡可能的大規模催化變革,所以最重要的是可以即時追蹤並做出反應的實際指標措施,以此來散佈觀念或建立可以更符合成本效益,來影響更多群眾的強大組織。那些資助社會創業家的人,可以自己看看受益族群獲得的好處,而他們通常認為,直接觀察是他們決定投資的充分基礎。更多嚴密的研究所帶來的精確性,通常都太耗成本也來得太慢。雖然可能會有無法控制的變數 (uncontrolled variables)、未預期的結果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或是無法估量的影響,但社會創業家與他們的資助人,似乎對於無法完整準確的測量到他們完整的社會影響這一點,並不怎麼感到困擾。 大部分的基金會,可能可以從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對「建立強大組織」與「大規模且快速的傳遞社會效益」這兩點的重視上,學習到一些經驗。基金會可以僅展示創新的模式,就仰賴政府廣泛採用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相反的,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主要依靠受資助者的自我報告,並在修改目標上允許保持彈性。但他們在很多不同的領域與地區工作的傾向,可能會限制他們建立專業能力、匯總績效成果 (aggregate results) 及獲得主流資助人信任。採納更嚴密的評估技術,可能可以讓他們更有系統地了解並強化支持他們變革的理論方法。 歸根結底,社會創業領域評估方法的崛起,對慈善事業整體上來說,是一個健康的發展。他們把我們的想法聚集在如何更快的幫助更多人這種實際的問題上,而本質上來說,慈善事業的目的就是幫助人群。 譯員A:許庭瑋 (3,516字) 2. 社會創業家與評鑑調查 你手中最大的利器,就是要能務實地適應改變。(要能視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 近年來「社會創業家」這個名詞,已經占據了一些主要基金會及私人資助者的想像力,並且在非營利領域快速的散播。有研究發現,該名詞在最近三年內,已在大眾媒體裡出現超過700次1。而大量的基金會、學者、非營利組織以及自認為是社會創業家的人們都已經崛起,並開始凝聚成一個獨特的學科。然而辨別社會創業家的因素,以及他們的資助人所使用的策略,又為評估調查帶來一系列新的挑戰。但資助人、思想領導者 (thought leaders) 及社會創業家們已經用他們的創新及洞察力,來對那些挑戰做出回應,並發展出可以符合他們需求的新方法;然而現在缺少一個機會來全面檢視這個領域,並且統合那些不同參與者累積、獨立發展出來的智慧。 這份報告追求的是在這個新興的社會創業領域中,收集各種盛行的評估方法,提供一些的範例,讓參與這個領域的人可以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學習,又或許可以對現階段更廣泛的慈善事業評估的思考有所貢獻。 我們的研究在2004年秋天進行,受訪者包含26位社會創業家、資助他們的基金會以及研究他們的思想領導者等(見:受訪人名單)。我們的受訪者雖只代表社會創業中的一小部分,但我們相信這些人對該領域中各種不同的方式與觀點具有代表性。若有受訪者積極參與評估調查行動的話,我們也要求及審查詳述評估過程的內部文件,同時我們也做了文獻審查。(見參考書目)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社會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及「評估調查evaluation」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更仔細的定義這些術語。 2.1 怎樣才算社會創業家? 「社會創業家」這個術語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定義,而且對評估調查來說,各自有不同的含意。這個術語最早是用來代表從一般非營利組織變得有「創業性entrepreneurial」,它們在本業之外,開創能獲利的商業活動來賺取收入 (to generate earned income)。理想上來說,該商業活動會與它的社會使命相關,但是主要的目的是賺取收入,所以要評估它的成功與否,可以直接看看它的盈虧 (bottom line)。 注釋:
1 Taylor, Hobbs, Nilsson, O’Halloran, and Preisser, The Rise of the Ter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Print Publications, Babson College, 2001. 2 “SROI”於此定義有別於 Emerson 的定義。社會創業領域術語的用法鬆散,代表的是此領域仍在早期發展階段。 Bibliography Acumen Fund. Performance Measures. Acumen Fund. Performance Scorecard. Ashoka. Knowing History, Changing It: Ashoka’s Theory of Change. Ashoka. Measuring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2003. Alvord, Sarah H., L. David Brown, and Christine Lett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 that Facilitate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An Exploratory Study, 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orking Papers, November 2002. AVINA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03. AVINA Foundation. Annual Survey Results, 2001. Bank of England. The Financing of Social Enterprises: A Special Report by the Bank of England, May 2003. Calvert Social Investment Foundation. Sample PRO Due-Diligence Template. Calvert Social Investment Foundation. SRO Project Brief. Cameron, Kim S. Effectiveness as Paradox: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Con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 May 1986. Community Wealth Ventures, Inc. Powering Social Change: Lessons on Community Wealth Generation for Nonprofit Sustainability, 2003. Community Wealth Ventures, Inc., Venture Philanthropy 2002: Advancing Nonprofit Performance Through High-Engagement Grantmaking, 2002. Dees, J. Gregory. Scaling for Social Impact: Design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Spreading Social Innovations,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uke University, The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 November 2003. Echoing Green. 2002 Fellows Mid-Year Report. Echoing Green. 2003 Fellows Year-End Report. ECOTEC Research & Consulting Ltd. Guidance on Mapping Social Enterprise: Final Report to the DTI Social Enterprise Unit, July 2003. Elias, Jaan. New Profit Inc. (Case Study),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at the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1999. Forbes, Daniel P. “Measuring the Unmeasurable: Empirical Stud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from 1977-1997.” New York Universit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June 1998. The Foundation Incubator. The Big, New Foundations: Their Leaders and Their Strategies, Summary Report, May 19, 2004. Fruchterman, Jim.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Social Enterprises. Fruchterman, Jim. “Technology Benefiting Humanity,” Ubiquity, March 2004. Gair, Cynthia. A Report from the Goodship SROI, 2002.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GEF: Second Overall Performance Study, 2002.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bsite. Gentile, Mary C. Social Impact Manage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or A Totally Different Currency? Initiative for Social Innovation Through Business, The Aspen Institute, fall 2002. Global Partnerships. Due Diligence Process, Information Requests, Business Plan Guide and Loan Agreement. Grameen Foundation. Grameen Connections, (Newsletter). Guidice, Phil and Kevin Bloduc. Assessing Performance at 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A Case Study, The 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 2004. Herman, Robert D. and David O. Renz. “Theses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June 1999. Johnson, Sherill. Literature Review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anadian Centr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November 2000. LaFrance, Steven and Rick Green. 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Theory of Change, July 2003. Leadbeater, Charle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 1997. McGrath, Rita Gunther and Ian C. MacMillan. “Discovery-Driven Plann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1995. NESsT. Venture Planning Grant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website. Paton, Rob. Manag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Enterprises,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feffer, Jeffrey and Robert I. Sutton. The Knowing–Doing Gap: How Smart Companies Turn Knowledge into Action, 2000. Pew Charitable Trusts.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at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January 2001. Reis, Tom. Unleashing New Resources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Common Good: A Scan, Synthesis and Scenario for Action, January 1999.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An Oasis of Information, 2002. Schmidt, Christoph M. Knowing What Works: The Case for Rigorous Program Evaluation, December 1999. Schoning, Mirjam. Global Trends in Financing the Social Sector: How Successful Social Entrepreneurs Mobilize Resources and Leverage Their Ideas,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ue Diligence Report, 2003.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Nomination Form, 2004.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certification Form.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creener’s Evaluation Form, 2004/2005. Schweitzer, Maurice, Ordonez, and Bambi Douma. “Goal Setting as a Motivator of Unethical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University of Montana, 2004. Seelos, Christian and Johanna Mai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ES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dad de Navarra, 2004. Wisely, D. Susan. “Parting Thoughts on Foundation Eval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2002. W. K. Kellogg Foundation. Evaluation Handbook, 1998. World Economic Forum. “Philanthropy Measures Up,” Global Leaders of Tomorrow, January 2003. 關於作者: 馬克•克萊門 (Mark R. Kramer) 係基金會策略諮詢顧問組織 (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 FSG) 共同創始人及總經理。FSG 是一家國際知名諮詢公司,在波士頓、舊金山與日內瓦都有辦公室。克萊門也是位於麻州劍橋的實效慈善事業中心創始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深研究員。克萊門與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波特,在哈佛商業評論共同發表兩篇深具影響力的文章:Philanthropy’s New Agenda: Creating Value (1999) 及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2002)。克萊門亦經常於主要刊物發表有關慈善事業的作品,包括: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慈善紀事報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捐助人雜誌 (Benefactor Magazine) 及基金會新聞及評論 (Foundation News & Commentary)。 在此之前,克萊門曾經從事創投資金投資人長達12年。克萊門以優異成績獲得布蘭代斯大學學士學位,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MBA學位,及以優異成績獲得賓州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 Fast Company雜誌與Monitor集團的 「社會資本家Social Capitalist」獎 2004年一月,Fast Company雜誌與Monitor集團合作出版了第一個關於25名頂尖「社會資本家social capitalists」的年度調查報告。這個術語是他們為那些使命驅使 (mission-driven) 的組織所創造的,這些組織都有很多我們歸類為社會創業家的特性。雖然該報告每年都在改進當中,但他們嚴格又考慮周詳的篩選過程,很多都與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提出的挑選標準相似。 每位候選人由五個基本範疇中的十八個標準來評分,但真正的分數主要是基於質化評量,然而每個範疇中,權重以及精確的標準,在過程中維持了一貫性、客觀性及紀律性。我們發現把這些標準放在一起看,它們很多都是在社會創業領域中定義「成功」的參數。 1. 社會影響:創造的重大社會價值,不論是絕對的 (absolute) 或是人均的 (per capita),以及能刺激制度改進的實證潛力 (demonstrated potential) 。實現社會影響的制度:組織對該議題的嫻熟程度、變革理論,以及組織用以評量自身影響力的方法的強度 。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的證據,包括影響的規模、廣度、深度以及難度 。制度的影響:對製造目標問題的基礎制度所帶來的影響,如政府政策、社會規範或產業慣例 。透過影響該領域所造成的非直接影響:對外接觸其他的組織以及知識與資料的散佈 2. 抱負與成長:達成長期更大(直接及制度性)影響的渴望與能力 。對造成直接影響的抱負規模:對不間斷的大規模成長有大膽想像的企圖心 。對制度性影響的抱負規模:除了在目標人口上的直接影響外,在該領域設定制度性影響的遠大目標 。致力於成長:證明成長的紀錄及組織進程,還有支持持續拓展影響的文化 3. 創業精神:不間斷的刺激內部與外部的社會影響資源,並開發因情勢轉變所造成的突變情勢 。刺激資源的能力:相對其他組織而言,能吸引大量資源的能力,並能有創意地讓個人及機構有積極主動,實現目標的動機 。有效率的使用資源:能以少做多的能力 。夥伴策略:選擇能拓展組織能力,並帶來更多成長的夥伴 。事先預料並適應改變:現行系統能尋求改變及創造快速的組織回應,來開發新機會的證據 。創業文化:一個有清晰遠見、熱忱、企圖心、創意、彈性及責任心的堅強管理團隊 4. 創新:一個組織的「大創意big idea」及其所提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的獨特性與力量 。「大創意」的力量:對解決社會問題新穎又強力的獨特看法,而且有潛力能隨時間增加其影響力 。商業模式中的創新:引領創新的營運系統或組織結構 。創新的效益最大化:產生新點子的能力,以專業態度決定要追求哪個想法,以及讓理想順利實現的能力 5. 永續性:長期維持已達成的社會影響及其相關商業模式的能力,包括達成組織成長抱負的商業模式的潛力 。資源策略:與整體商業模式及變革理論有密切關係的多元及可再生的收益來源 。管理與營運實力:具備能發揮實際功效的董事會與管理團隊、延攬專業能力人士的能力、對經營環境的洞察力及有說服力的成長策略 。應變能力:提前分辨潛在挑戰並有彈性的應變能力 「拱心石 Keystone」組織:標準化績效評量 有關社會效益的通用評量,長久以來一直是社會創業資助人的美夢,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朝那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對受資助人也很有用,那一步就是呈報 (reporting) 的通用架構。這樣的標準化,會大大的增加社會企業的責任性 (accountability) 與透明度 (transparency)。這個方法將使得在相同領域與地區的組織,進行有意義的績效比較;但目前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兩年前(2004),大衛•邦布萊特 (David Bonbright) 內心懷抱這那樣的目標,建立了「拱心石Keystone」組織(原名ACCESS),開發了一套在全世界的公民社會、非營利領域以及公益組織裡,整體通用的呈報標準。他曾說: 我想,在社會組織裡,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完成一個更好的績效評量系統來的重要…若捐贈者覺得這個部門,整體來說,對責任性草率處理,反抗的阻力就會拖累援助。」 每位資助人現在以呈報規定 (reporting requirements) 作為資助的應變根據,而結果是非常沒有效率的多重呈報規定。公民社會組織對每位捐助者呈報的方式都不同,以致造成混淆、重複甚至是濫用;我們想要換一個別的系統,在這系統所有的資助人都用同一組呈報原則。 拱心石的做法是提供方法、工具及系統給類似的組織,讓他們得以建立自己的呈報標準。舉例來說,我們在南非與一群愛滋計畫及其資助人合作,他們會全體一起經歷整個過程,然後想出一個呈報模式,這個模式是他們相信全南非的愛滋組織都會想使用的。再舉另一個例子,就說我們在孟買幫助無家可歸的人好了,我們集合所有的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當局,製造出定時標準化呈報系統的體制資料,然後我們收集來自政府及學術調查等等的總體經濟數據,定期把資料組合並做出趨勢線,這就是計畫累計的影響,而這是問題所在,但願你能看到兩條線慢慢相交。若你做到了,人們對於「贈予giving」會做出不一樣的決定,他們會說:「嘿!我們真的在世界上解決這件問題。」,若我們深入研究,就可以知道哪個組織做的改變最大,而且也刺激其他人採用那些策略。 更多資訊查詢請到www.accountability.org.uk. REDF: 計算投資的社會報酬 杰德•愛默森 (Jed Emerson) 在羅伯特企業發展基金會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REDF) 及惠普基金會 (William &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領導了大量的研究,定義「投資的社會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他提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間是有連貫性 (continuum) 的。經濟效益很容易測量,但純粹的社會效益可沒那麼簡單。然而存在它們之間的是社會經濟效益 (socioeconomic benefit) 的領域,這是一種「融和價值blended value」的形式,有些構成要素可以測量,有些則不行。 例如,一個就業輔助計畫產生的經濟效益,可以簡單的透過加總政府結存的就業津貼,以及每位成功取得長期就業機會的扶助對象所繳的所得稅來統計。只要經濟效益比那些投注在訓練失業人口,並輔導就業的組織的慈善資源還要大的話,那麼投資的社會報酬就是正面的,而且也可能確實很可觀;其他可能形成的社會效益,例如更大的自信或幸福感、孩童們有更穩定的家,諸如此類,並不能用類似的方法測量。 因此艾默森建議,所有的投資都應該要有正面的投資社會報酬,但因為社會效益被排除在外,所以他又建議計畫不能只用社會報酬來比較或排名。正如杰德的共同作者美琳達•團 (Melinda Tuan) 所言: 羅伯特企業發展基金會的投資社會報酬評量,它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讓你拿SROI報告與其他的報告相比;我們只是想看看它們是否都是正面的。審視投資組合,全部都有正面社會報酬的機會有多大?但每個社會目的企業最後都有正面社會報酬,他們全都值得投資。根據SROI,我們得以控制風險〔並〕獲得正面報酬,所以我們持續投資,也鼓勵他人投資。 最後,REDF的經驗是,用嚴謹的紀錄方式,精準地計算SROI是非常複雜與昂貴的作業。他們為受資助人發展的系統,有重要的附帶益處,那就是提供能促進每日營運的詳細管理資訊,但追蹤過去的受惠人帶來大量的額外成本。考量成本與複雜度的關係,我們並沒有在其他資助人中找到使用這個工具的人。 我們的資助對象會做這評量,是因為我們是夥伴並且給他們經費;但當營運變得棘手,這就不是利用大家時間最好的方式,特別是SROI:它很耗時,甚至最後也不會在報告他們的計畫推行度或企業營運上有特別的幫助。要向資助人解釋,並讓他們了解報告也很難,而最後,對幫助他們的企業籌募資金的組織,也沒甚麼幫助。 關於投資社會報酬評量 (SROI) 的更多資訊請至www.redf.org About the Skoll Foundation 思高基金會 總部設在美國加州 Palo Alto 的思高基金會,在 1999 年,由 eBay 的第一位員工暨第一位總裁,傑夫•思高 (Jeff Skoll) 所創立。其創立使命是透過投資、聯繫及表揚社會創業家,以推展制度性的變革;這些社會創業家致力於創造新的解決方法,以期能為世界各地社區帶來長期的生活改善。 思高基金會投資社會創業家的方式是主辦三個獎項計畫。基金會聯結社會創業家的管道是透過線上社群Social Edge,及在牛津大學的思高社會創業中心所舉行的年度思高社會創業世界論壇 (Skoll World Forum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在2005年公開播映的公共電視紀錄片「新英雄The New Heroes」四部曲是它表揚社會創業家的途徑之一。 更多資訊,請至:www.skollfoundation.org. About FSG Social Impact Advisors FSG 社會影響諮詢顧問 FSG 社會影養諮詢公司係一非營利組織,從事推廣慈善事業及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於促進社會進步,其方式有三:
FSG 社會影響諮詢顧問係由馬克•克萊門 (Mark R. Kramer) 及麥克•波特 (Michael E. Porter) 教授於1999年以「基金會策略顧問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之名所創立。 更多資訊,請至:www.fsg-impact.org 譯員:許庭瑋 翻譯機構: 台灣社會公益行動協會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本文版權歸原作者及原網站所有。本網站翻譯文章僅供個人使用。 如需下載,請尊重著作財產權,不得轉為營利用。
0 評論
發表回覆。 |
地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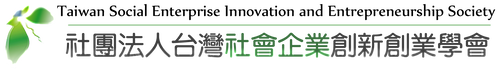
 RSS 訂閱
RSS 訂閱